国外企业年金监管研究综述
何 伟(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北京 100872)
企业年金作为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目标中的第二支柱,其作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加强了有关企业年金监管的研究。企业年金简单来说,就是企业向职工提供的养老金。最早的企业年金产生于18世纪的美国,当时美国政府向那些在独立战争中致残的士兵支付年金作为其生活来源。正规的企业年金计划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运通公司1875年建立了第一个企业年金计划,向那些在工作中致残并在该公司连续工作20年的职工提供年金待遇。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政府开始大力发展企业年金,以此来缩减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减轻政府负担,同时也为国民提供了一条增加养老金的有效途径。由于企业年金在保值、增值的过程中存在种种风险,就必须对其实行严格和有效的监督、检查。现在各国政府对企业年金实行监管大致有两种模式:一是审慎监管模式;二是严厉监管模式。
一、概念界定
年金是指在一定年限内按年度(或按期)支付的一定数额的现金收益,通常是指以保障退休后(养老)收入为目的的收益。企业年金(Corporation Pension),又称“雇主年金”或者“职业年金”,顾名思义就是企业向职工提供的养老金,或企业退休金。具体而言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公共养老金或国家养老金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旨在为本企业员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补充性养老金制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将社会养老保障概括为三个支柱:第一支柱是政府基本养老保险,主要是指政府强制实施的国家公共养老保险计划系统。第一支柱的目标是保障社会成员或一定范围内的退休者的基本生活。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总体上泛指企业雇主对雇员实施的养老金计划,一般与就业相关联。企业年金养老待遇与缴费和投资回报率相联系,更多地体现效率机制,一般缴费越多,回报越高,待遇也就越高。第三支柱是个人自愿性的养老计划安排,一般为自愿储蓄型,是对第一、第二支柱的补充。
监管是指一般照看、监督或检查。管理是指决定、确立或控制;依一定规则或限制进行指导;受管理性原则或法律的管辖。[①]企业年金监管是指企业年金监管机构对企业年金运营机构和投资运营活动进行决定、限制和约束的一系列行为的总和。对企业年金的运营实行监管,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即便是企业自主建立的企业年金计划,其顺利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在一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企业年金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养老保险的主要支柱,瑞典、荷兰1997年的企业年金资产甚至超过了这两个国家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②]。企业年金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有关企业年金监管的研究、讨论也越来越多。本综述主要从企业年金的产生、为什么要对企业年金运营实施监管以及如何对企业年金进行监管这三方面的理论进行梳理,来对企业年金监管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二、企业年金的产生
据资料记载,最早的企业年金在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后就曾出现,当时美国政府向那些在独立战争中致残的士兵支付年金作为生活来源。正规的企业年金计划是从19世纪晚期开始出现,1875年美国快递公司建立了第一个企业年金计划,向那些在工作中致残并在该公司连续工作20年的职工提供年金收入。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大约出现了400多个企业年金计划。历史经验证明,大部分企业年金计划是由雇主先提出的,不是社会压力、政府主导的结果,企业举办企业年金的目的非常简单:一方面是为了享受税收优惠,从而壮大企业自身的资本实力;另一方面是为其雇员提供更多的福利待遇,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19世纪末,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企业年金计划,有关企业年金方面的理论也开始出现。埃佛里特·T·艾伦把雇主建立企业年金的动机归结为雇主父爱主义传统。企业文化是竞争的文化,即企业参与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和企业内部“对立统一性的劳工关系”的反映。在这一竞争环境里,雇主希望消除或减轻与雇员之间的摩擦,改善他们的关系,鼓励雇员努力地安心地工作,并节约生产经营成本,雇主把雇员视为“不够理智”的孩子,通过建立具有激励性、凝聚力的企业年金计划来实现上述目的。在分析雇员加入企业年金计划的行为时,艾伯特·安多(Albert Ando)和佛朗哥·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等学者认为企业年金制度是人们储蓄活动的替代物。这一理论把人的整个生命过程划分分为工作阶段和退休阶段,人们在心理上总是试图将其所掌握的资源在一生中进行适当的分配,以便使消费在一生中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年金制度的出现是为了方便人们的储蓄活动,是通过年金的缴纳与退休金的支取,以替代以往人们的储蓄行为。从政府方面考虑,西方发达国家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日益成熟,现收现付制的政府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难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财政又无法填补这一“无底洞”,于是各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企业年金计划,以此来缩减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减轻政府负担,同时也给国民提供养老保障的一条有效途径。国家、企业和个人分别举办养老保险在国外目前已十分普遍。国外的实践证明,这种“三足鼎立”式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大大减轻政府养老的财政压力。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博迪(Zvi Bodie)等人所指出的[③] “政府只应向全体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经济保障,而不应当不考虑个人的偏好和殷实程度一概而论地向他们提供过高的保障水平。在政府提供的最基本的经济保障的基础上,老年人可以通过企业年金或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来取得额外的退休收入。”
三、对企业年金实施监管的必要性研究
企业年金具有养老保障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企业年金计划受益人的未来受益应该具有确定性,因此,在企业年金运营过程中应将安全性放在首位。但是为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把积累的资金进行投资运营,实现企业年金基金的保值、增值,这又不可避免地把企业年金基金暴露在风险环境之中。企业年金的风险就是个人年金账户的资产实际价值下跌,或者投资它们获得的收益低于可能理想收益水平的可能性。关于企业年金运营过程中风险分类的方法很多,但一般都归为两类:一类是外部风险,一类是内部风险。外部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制度风险,内部风险包括道德风险以及实施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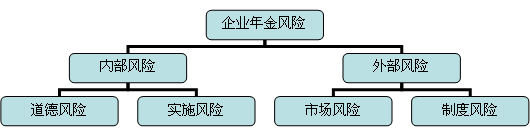
图1.企业年金的风险系统图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企业年金运营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④]。之所以会产生道德风险这种现象,是因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拥有独家的信息。阿罗(K. Arrow)把这类信息优势划分为“隐蔽行动”和“隐蔽信息”。前者包括不能为他人准确观察或臆测到的行动,后者则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对事态的性质有某些但可能不够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足以决定他们采取行动是恰当的,但他人不能完全观察到。企业年金运营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知道企业年金基金的实际财务状况,而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和监管机构不了解(因为他们不直接参与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管理);并且企业年金的委托期较长,从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缴费到企业年金计划受益人领取待遇之间有一段20年到40年不等的时间间隔,这更加剧了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与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就为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产生道德风险提供了方便。
企业年金运营过程存在着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方面,参与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委托受托人管理资产,形成第一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另一方面,受托人将基金资产委托给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形成第二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正是由于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就为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产生道德风险创造了条件。
企业年金基金的所有者(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与企业年金基金的管理者(受托人、投资管理人、托管人)是具有不同利益的经济主体,受托人、投资管理人、托管人比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来说掌握更多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如果企业年金计划的委托代理关系设计不当,很有可能发生年金投资管理人侵犯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的情况,甚至投资管理人、托管人和受托人合谋损害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的情况,从而产生典型的道德风险现象——“内部人控制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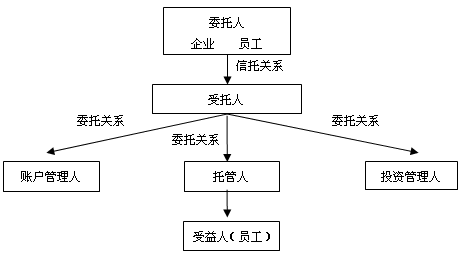
图2.企业年金基金的委托——代理关系图
在企业年金投资运营过程中,除了内部治理风险之外,还必须考虑实施风险(可分散风险)和市场风险(系统风险)。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上有多种多样的投资工具可供养老基金选择。将基金存入银行生息和购买政府债券是两种最传统的投资工具。此外,养老基金还可以购买企业债券、公司股票、住房抵押贷款以及海外股票等。养老金基金传统上购买的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共债券。这种债券价格便宜、容易进入市场、利息稳定,因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相对于公司债券而言,公共债券的回报率通常要低一些,因此,成熟的养老基金往往倾向于较少购买和持有政府债券,较多地购买公司债券。公司债券比公共债券的风险要大,但回报率也高。要实现企业年金投资年金项目的高收益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在企业年金投资运营过程中,托管人、投资管理人、外部顾问由于不能胜任工作、沟通不畅、投资行为不稳定等原因,很可能给企业年金造成财务上的失败。对于这类风险,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可供选择的投资策略以减少高风险对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产生的影响,其中一些策略非常简单,如对不同类别的资产采取投资上限、规定最低资本金要求,以确保养老金资产恰当的资产组合分散化以消除非系统风险、,只留下市场风险。
监管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确保企业年金资产组合分散化,同时把某些风险太大且没有流动性的资产排除在资产投资机会之外。不过,即使在进行恰当的分散化之后,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仍然面临着市场风险。这可能归因于各种因素,例如,利率变动,通货膨胀、汇率波动等。时间跨度和持有期间越长,市场风险显现的可能性越低。
制度风险包括企业年金计划中的设计缺陷,政治压力对企业年金投资决策的影响,缺少相应的企业年金运营的法律、法规。在竞选年度快要来临时,政策制订者可能为了连任,过分注重短期目标,而忽视企业年金长期收支平衡。
由于存在上述风险,因此,为了保障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的利益必须对企业年金基金运营实施监管。从国外研究情况来看,对企业年金进行监督和检查成为一种“公共商品”,需要政府制定法律、法规规范企业年金的运作,并建立权威机构对企业年金进行检查和监督。
四、企业年金监管研究
由于企业年金运营过程中面临上述风险,因此对企业年金的运营实行监管,已成为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世界各国通常根据本国的企业年金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一般从以下两种模式中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企业年金监管模式:其一是审慎监管模式(prudential regulation mode)。即根据审慎性原则对企业年金进行监管。这种监管模式适合于经济发展比较成熟,金融体制比较完善、资本市场和各类中介组织比较发达、基金管理机构有一定程度发展、相关法律比较健全的国家。在这种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较少干预基金的日常活动,只是在当事人提出要求或基金出现问题时才介入;在很大程度上,监管机构依靠审计师、精算师、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组织对基金运营进行监管。其二是严厉监管模式(draconian regulation mode)。这种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强,一般都是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这种模式除要求企业年金运营机构达到审慎性监管要求之外,还对年金的治理、运作和绩效等具体方面进行严格的限量监管。
在先行的契约结构安排中,受托人购买收益凭证时托管人已经由基金管理公司选择好了,如果托管人监管过严,那么投资管理人就会选择别的托管人。因此,谁选择托管人关系到托管人对谁负责的问题,要改善内部人控制现象必须改变由投资管理人选择托管人的做法,由受托人分别和投资管理人、托管人签订契约,让托管人制衡和监督投资管理人。
但是具有相互独立经济利益的托管人、投资管理人的行为是难于观察和准确度量的,怎样才能使得他们各尽其职,帮助受托人完成各项委托任务呢?让代理人拥有一部分剩余索取权(实施上也就是承担一部分受益风险)是形成激励兼容的最好办法。[⑤]另外规定投资者可以自由转换基金,设立竞争性的基金经理人市场,运用市场力量,对投资管理人形成外在的压力,以使其规范投资运营行为,这也是对企业年金中“内部人控制”的一条有效治理途径。
企业年金基金在市场中进行投资运营过程中存在投资风险,且投资风险与预期回报率呈正相关关系,投资风险越大,投资的潜在回报往往越高,因为大多数的投资者在没有高回报保证的情况下不会进行高风险投资。市场相应地为投资定价,如果养老保险计划想要减少投资风险,它就要选择保守的投资,但是这样会减少投资回报。投资回报率是公众衡量一个企业年金计划的主要参考指标,如果一个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投资回报率过低那么对公众来说是缺乏吸引力的,有可能导致公众选择其他的投资管理人。因此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有将年金资产投向预期收益较高资产的激励,这样也将年金资产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下。有些公司虽然规定员工有决定自己个人账户资金投资方式的自由,但往往公司提供给员工的退休基金投资方式是包括自己股份在内的几个单调组合,而且购买本公司股票又能享受价格上的优惠,面对十分有限的选择,员工用自己大部分、甚至全部的退休金去购买公司股票。他们忘记了关键的问题:资产组合和分散风险。一旦公司破产,员工就会陷入养老保障与工作一起丢的困境。因此建立企业年金计划国家无不对企业年金投资进行管制。管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年金运营机构的资格认定、风险、所有权集中和资产类别的持有上限。这四项被认为是毫无争议的谨慎性原则。这些原则被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荷兰的企业年金监管体系被认为是严格遵循“谨慎人”原则。它只要求那些负责任的管理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要勤奋,要具有专门技能,并且要慎重考虑基金的特殊环境,附带条款通常是大致分散化的要求和忠诚义务(只考虑受益所有者的利益)。另一类发达国家和所有的拉美国家对资产类别实行了限制,这些国家的投资管制被贴上了“量化”或“严格”的标签。这些管制通常具体规定了养老基金可以投资资产类别的最大数额,有些国家还规定了资产的最低持有额。
国外有研究表明进行内容广泛的信息披露,有助于减轻企业年金风险。信息披露的目的是为了使职工能够做出有根据的选择,并向基金经理施加压力,使得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置于企业年金计划委托人和监管机构的双重监管之下,这样还使得年金转换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职工离开一只基金时的账面余额应该反映所有的以市价为基础的资本盈利和亏损,包括实现的和未实现的)。尽管大量的基金之间的转换看上去更多地所市场动力的驱动,而不是对收益和成本进行客观比较的结果,但是,信息披露要求本身就是这些计划的一个有吸引力的特征。
不同群体对企业年金计划有着不同的需要,比如说老年职工需要风险较小、流动性较高的企业年金资产组合,而年轻人则可能需要收益性较高,对流动性无特别要求的资产组合,由于所有可利用的资产组合基本上相同,职工无法在各种风险—收益组合之间做出有意义的选择,因此,年轻职工和老年职工被迫持有相同的资产组合。对此可以建立面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企业年金计划。这样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对企业年金计划的需要,降低制度风险。
企业年金与其他基金相比,有更长的投资周期,而且对企业年金流动性要求也不高,放宽对企业年金(如国外证券、风险投资等)的投资限制,有助于企业年金投资运营获得更高的潜在收益。但是如果这样,监管部门的风险管理过程会变得非常复杂,而且使企业年金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之中。因此,适当地放松监管与适时加强投资限制相结合对企业年金成功运作至关重要。28但是,当政府是出于某种内部的目的而决定对养老保险基金实施某一管制措施时,其结果往往可能是报酬递增的。例如,管制成本的存在,可能会使政府并不采取成本最小化的方式,而是继续加强管制,以寄希望于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弥补管制成本,在类似的情况下,政府管制本身就会产生一种自增强机制,逐渐使管制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最终使其边界超出原先弥补市场失灵得范围。布赖恩·阿瑟(Brian Arthur)研究发现,对养老基金经营决策活动干预过多,反而会影响基金管理者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导致非市场失灵。戴维斯·E·菲利普(Davis E. Philip)通过研究发现在谨慎人环境中的养老基金的实际投资回报率高于更严格的限制环境中运作得基金,尽管投资限制不能够完全解释投资回报率的差异。(因为在许多国家这些限制是没有约束力的),但这还是主要归因于他们的资产组合中有较大份额的股票。如果投资限制妨碍了分散化,并且使基金成员暴露于更大的资产组合风险之中,结果基本上是适得其反。S.P. 斯里尼瓦斯(S.P. Srinivas)和J.叶尔莫(Juan Yermo)通过对拉美国家年金的投资收益和基金投资限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较早进行养老体制改革的智利和秘鲁分别有相当一段时期,其年金的投资收益低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指数等市场基准指数(market benchmark index)的增长率,有时甚至低于银行定期存款的收益率。智利放松对企业年金投资的限制以后,基金的绝对收益和相对于基准指数的收益都上升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智利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率几乎年年提高,到1999年6月,基金资产的61%是投资收益形成的,只有39%来自缴费。如果各国规定的养老金资产组合的数量限制过严,过于具体,则将限制养老基金资产管理人投资时在风险和收益之间进行选择,这可能会迫使他们持有一些较为安全但收益率很低的资产,而且还可能会损害养老基金发展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埃佛里特·T·艾伦等:美国退休金计划(第8版),杨燕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崔少敏等:《补充养老保险——原理、运营与管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
3.耿志民:《养老保险基金与资本市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4.刘世锦等:《中国养老保险模式选择与养老保险金进入资本市场问题探讨》,《管理世界》1997年第3期。
5.刘钧:《美国企业年金计划的运作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9期。
6.刘文海.《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47-48页。
7.唐旭等:《中国养老基金的投资选择》,《金融研究》2001年第1期。
8.王信:《养老基金运营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9.于洪:《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财经研究》2002年第9期。
10.杨燕绥:《企业年金理论与事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
11.张俊山:《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年金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2.Brian Arthur :“The Self 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经济学中得自增强机制》,中文译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5期。
13.《布莱克法律词典》(第五版),西部出版公司1979年版。
14.《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
16.Akerlof, G., 1970, “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4(3), 488-500.
17.Albert Ando and Franco Modigliani. 1963. “The Life-Cycle’s Hypothesis of Saving: Aggregate Implications and Te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3, 55-84.
18.Arrow, K., 1985. The economics of agency. In Principles and Agents: The Structure of Business, ed. J. Pratt and R. Zeckhauser,
19.Bodie, Zvi, Merton, R.C. and Samuelson, W., 1992, “Labor Supply Flexibility and Portfolio Choice in a Life-Cycle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6, 427-449.
20.Canadian Association of Pensio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CAPSA Pension Governance Guideline and Implementation Tool, 2001.
21.
22.Juan Yermo, 2000, “Pension Funds in
23.Krishnamurthi and Sudhir, 1999, “Applying Portfolio Theory to DB and DC Plans”, Paper presented at World Bank Conference .Pension Syste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Achieving Effective Fund Management.
24.Laboul A., 1999, “Private pension systems: regulatory policies”, Ageing Working Paper, AWP 2.2, OECD, Paris.
25.Martin J. Gruber, 2000, “Identifying the Risk Structure of Mutual Fund Returns”, European Financial Management, 7(2), 147-159.
26.Queisser and Monika, 1998,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Pension Fund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Vol.51, April-June, 1-21.
27.Richard A. Posner, 1994, Economic Analysis of
28.Roberto Rocha, Joaquin Gutierrez and Richard Hinz, 1999, “Improving th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of pension Funds: Are There Lessons from the Banking Sector?” September, 32-35, http://www.worldbank.org/html/dec/chiefecon/conferen/papers/bankpen.pdf.
29.Stanistawa Golinawska and Piotr Kurowski, 2000, “Rational Pension Supervision”, CASE Reports, No.36, 8-9.
30.Srinivas, S.P and Juan Yermo,
31.Srinivas, S.P and Juan Yermo, 1999b, “Do investment regulations comprise pension fund performance?”, http://www.worldbank.org/wbi/pensions/courses/march2000/proceedings/pdfpaper/week2/valdes.pdf.
32.Shooley, D.K and Worden, D.D, 1999, “Investor’s Asset Allocation vs. Life Cycle Funds”, 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 55(5), 37-43.
33.Vittas and Dimitri, 1998, “Regulatory Controversies of Private Pension Funds”, Development Research Group, the World Bank, January, 1-36.
[①] 《布莱克法律词典》(第五版),西部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528页。
[②] 1997年,瑞典企业年金占GDP的比重为117%,荷兰企业年金占GDP的比重为102%。资料来源:Juan Yermo, 2000, “Pension Funds in
[③] Bodie, Zvi, Merton, R.C. and Samuelson, W. 1992, “Labor Supply Flexibility and Portfolio Choice in a Life-Cycle Model”,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6, 427-449.
[④]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8页
[⑤] 加拿大企业年金计划中采取了这种办法,由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很多国家都纷纷仿效,以此来解决企业年金运行中出现的“内部人控制”现象(Canadian Association of Pensio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CAPSA Pension Governance Guideline and Implementation Tool ,2001)
“国外企业年金监管研究综述”由中国社保网收集整理编辑。
本文地址:http://www.shebaodata.com/xinwen/95827.html
为了社保知识的普及、信息的传播,中国社保网欢迎您转载分享。但请注明文章出处并保留完整链接。否则我们将保留追究其版权责任的权利!
社保常见问题答疑
最新刊登
- 苏州单位社保缴纳个人一年4314元,缴纳23年退休工资一个月 2025社保退休工资计算公式 四川眉山养老金计算公式2025计算 社保交33年退休金今年有多少?(2月5日) 2025年,养老金即将上涨,工龄27年、32年、37年,领的钱差 湖南益阳退休人员2024年养老金计发基数出炉 养老金重算补发 广东佛山交16年养老保险每个月能领多少? 申领失业保险金需提供的材料?大理的申请失业金材料要求一 2025阿勒泰退休工资计算公式,27年退休金多少钱? 社保缴费24、29、32年区别有多大,谁领的养老金多? 喀什退休金计算公式2025,16年能享受到多少养老金呢? 25年工龄退休工资是多少?(2月5日) 退休金和养老金有区别吗?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金多少钱一个月 社保缴纳年限有何要求?福鼎社保多少钱一个月2025年? 2025年,养老金即将上涨,工龄28年、31年、32年,领的钱差 公积金房贷利率会自动调整吗?静安调整时间是什么时候? 2023-2025年湖北咸宁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湖北咸宁社保需要缴 2025南京退休养老金账户金额怎么计算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 东方社保交28年可以领多少退休工资? 青海西宁退休金计算方法,缴纳攻略如何交更划算你知道吗? 昌都住房公积金单位和个人缴纳比例是多少?有封顶吗?最高 线下办理失业金领取需要本人吗?伊犁的失业金领取要求? 社保缴纳20年,能有多少退休金?(02/05) 北京养老金重算补发,哪些人能领取?北京养老金计算公式是 社保交满15年每月领多少钱?19年、24年和29年工龄退休分别 2024~2025年陕西榆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最新标准(申请条件+ 运城缴纳200%档26年社保,领多少养老金?(25年2月5日) 2024-2025年新乡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价格表 新乡灵活就业 社保交满37年、40年和42年退休,哪个退休金高?举例说明 浙江衢州养老金计算公式2025年计算举例 2025年浙江衢州退休 解密2023年甘肃金昌养老金计发基数之谜,养老金迎来重算补 社保断交后可以补交吗?(02/05/25) 灵活就业自己交社保一个月要交多少钱?02/05/25 鹤岗交多少个月失业保险可以领失业金? 2025年鹤岗失业金领 2025年汕头五险一金的缴费基数是多少(缴费基数+缴费比例) 换工作期间社保断交一个月怎么办?(2月5日) 公积金利率下调2024,山西晋城2024年贷款利率,房贷100万利 住房公积金个人缴费上限是多少?广东韶关公积金2024年缴费 陕西延安社保待遇认证怎么在手机上完成?最新教程来了(怎 汕尾4050社保补贴标准最新消息 2025年汕尾灵活就业4050补贴 2025安康社保缴费标准一览表(2025-02-05) 失业金停止领取的条件是什么?2024年景德镇的失业金申领条 天津交灵活就业社保与职工社保有什么不一样?天津灵活就业 永州社保缴纳到退休能领到多少钱?2024-2025年永州社保缴费 贵港失业保险金怎么申领?来看→ 公积金贷款利率2024最新消息 克州首套房五年以上公积金贷款 武威公积金缴纳比例基数是多少?最新住房公积金基数何时调 防城港4050社保补贴多少钱一个月,2024-2025年4050社保补贴 南充公司社保可以不交吗? 社保中断了几年还能续交吗?(2月5日) 谁能领失业保险金?海拉尔失业金领取要求标准 社保断了七八年能续交吗?(25年2月5日) 社保缴纳基数是按照实发工资还是应发工资缴纳?个人需要交 广东河源社保缴费比例是怎样的?广东河源社保计算公式一览 2025新农合怎么报销?2025年新农合的报销流程和标准是多少 最新保亭公积金缴纳标准一览表,2024-2025年公积金缴纳基数 离职失业金怎么领取?承德的失业保险金申请要求 内蒙古乌兰察布房贷利率调整新消息 现在 内蒙古乌兰察布存 2024-2025年东城灵活就业社保每月需要多少钱?自费灵活就业 2024~2025年张家口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最新标准(申请条件+申 2025社保个人缴费标准多少钱,社保个人缴纳多少钱一个月? 社保断交就作废了吗?2025年南充社保多少钱一个月? 文山市失业金怎么领取需要什么条件和手续?这里整理收好了 2025昌都社保缴纳比例是怎样的?(2025年2月5日) 2025年商洛公积金个人公积金缴存多少?商洛公积金缴存基数 2024~2025年烟台灵活就业4050补贴最新标准 烟台灵活就业社 2024-2025年阿拉尔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标准:自费社保需要 张家口失业金领取条件及标准 最新张家口失业保险金在哪里可 曲靖申领失业保险金需提供的材料哪些? 2025年柳州社保缴纳比例,2025年柳州社保缴费多少钱?2025 公积金利率下调2024,安徽阜阳2024年贷款利率,房贷100万利 2024公积金缴费基数是多少 襄阳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 2024~2025年辽源4050社保补贴标准是多少钱一个月(失业金和 2025社保缴纳比例是怎样的?(2025年2月5日) 河北衡水失业金申请方式有几种? 社保缴纳多少年可以领养老金?(2月5日) 养老保险断交了3年怎么办?社保断交有什么影响?(2025年2 打工人缴纳社保缴费多少钱?2025年2月5日 2025铜仁社保缴费基数和比例是多少呢?(02/05) 西宁个人社保一个月多少钱?(2025/02/05) 社保一个月交多少钱,在职人员缴纳多少钱一个月?(02/05) 养老金什么时候发,有统一时间吗?02/05 安阳社保多少钱一个月?(02/05) 社保和农保都交了怎么办?(25年2月5日) 怎么算每个月五险一金扣了多少?(02/05) 2025北京社保缴费标准及比例是多少?(25年2月5日) 社保断交有什么影响个人可以补吗?(2025年2月5日) 社保停了几年怎么续交(02/05/25) 铁门关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一个月交多少钱?2025年2月5日 五险一金扣多少钱一个月 五险一金每月缴费怎么算?(02/05 退休养老金计算公式是怎样的?02/05/25 社保断交多久就作废了?(02/05) 浙江社保多少钱一个月?(2025-02-05) 换工作中间断了一个月社保怎么办?社保缴纳多少年可以领取 社保卡过期了?教你如何轻松换卡?(2025年2月5日) 2022银行购房贷款利率调整时间 西双版纳新商贷利率定价机制 申领失业保险金需提供的材料?娄底的申请失业金材料要求一 失业金在哪里怎么申请领取?最新吉林松原的失业金领取条件 上调吗?陵水公积金年度调整开始!有何变化? 上海失业金支付宝怎么申请领取流程?附失业保险金办理操作 云南大理2024年买房贷款利率怎么计算?房贷90万分30年本息 失业咋办?失业保险谁能领?长兴失业金领取标准 丰都公积金缴存基数怎么计算的?2024住房公积金基数工资标 张家口的失业保险金怎么申请?附失业金微信申请流程图 广东梅州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怎么查?2024首套、二套房公积 领失业金需要带什么材料?看看武威失业保险金办理材料一览 汕头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最新),2024-2025年汕头公积金个 内蒙古呼伦贝尔怎样在手机上申领失业保险金?支付宝领取失 公积金利率下调2024,河南洛阳2024年贷款利率,房贷100万利 抚顺公积金缴纳比例基数表 2024个人缴存一个月多少钱? 贵州遵义失业金发放标准提高?查询一下 贵州遵义失业金领取 贵港失业金领取标准2024年 贵港失业金领取金额怎么算? 青海海东房贷利率调整新消息2024 青海海东公积金商业贷款利 2025年丰县失业保险金线下可以办理吗?具体怎么操作? 2024-2025年银川职工住房公积金要交多少(缴费比例+缴费基 失业金怎么申请领取?掌握一下领取聊城的失业保险金要求? 2025年石嘴山失业保险金能线上申领吗?办理入口都有哪些? 更灵活!个人房贷利率重新定价了!广东茂名存量房贷利率调 静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定了么?2025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 2025年乌兰察布申领失业保险待遇,需提交哪些材料? 公积金利率下调2024,山东济南2024年贷款利率,房贷100万利 甘肃张掖:甘州区人社局为群众奉上人社“自助餐” 2025年新农合报销比例最新标准是多少 新农合门诊报销和住院 65岁老人住院报销比例是多少 新农合65岁以上的老人住院报销 新农合医保报销比例2025最新标准,最新消息 2025农村医疗保 深圳退休医保按月或一次性补缴要缴多少?哪种方式更好? 退休人员医保将有变化!2025年起医保划转金额提高能有多少 2025年起,退休人员医保划转金额有提高,能涨多少?提前了 2025年医保返款标准调整,退休人员年满70岁,返款金额能有3 2024年退休人员,医保个人账户返款标准有多少?会有所增加 2025年退休后医保卡每月打多少钱 2025年起医保划转金额新变 山西晋城:让就业社保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新农合(医疗保险)报销比例2025年最新标准,最新消息 新农合异地就医可以报销吗?2025年新农合异地就医报销流程 新农合异地就医报销流程2025最新消息 新农合异地就医可以报 新农合异地就医报销流程2025年最新是什么 新农合异地就医可 2025年新农合报销标准及范围是多少 最新标准 新农合医保报销比例2025最新标准是多少 2025农村医疗保险如 新农合门诊报销和住院报销标准多少?2025年新农合报销比例 2025年新农合生孩子可以报销多少?2025年新农合生孩子报销 新农合报销比例最新标准多少?2025年新农合门诊报销和住院 新农合报销标准及比例2025最新消息,最新标准 2025年新农合缴费价格是多少钱?新农合报销比例2025年最新 新农合二次报销标准及比例是怎么算的 2025年哪些情况不能报 生孩子新农合报销范围及标准最新消息 2025生孩子新农合可以 甘肃张掖:甘州区失业保险强服务 助企纾困促发展 2025年全国产假新规有多少天 2025年职工最长休假达1年(最 2025年厦门生育津贴能领多少钱 厦门产假多少天2025年新规( 重庆生育津贴领取条件及标准2025最新 重庆生育津贴128天还 2025生育津贴领取条件及标准 生育津贴2025年新规最新消息 2025年最新生育津贴领取条件及标准是什么 2025年生育保险报销最新标准 生育保险报销条件是什么 杭州生育津贴领取条件及标准2025年最新(领取条件+领取标准 2025生育保险领取要满足哪些条件?不生孩子生育保险就白交 广东产假法规2025年最新标准 广东省产假2025年能休多少天 浙江生育假多少天2025年新规最新消息 浙江产假2025年有多少 产假及工资新规2025 产假多少天2025年新规(最新标准) 全国产假新规2025年有多少天 2025年职工产假最长休假达1年 2025年厦门生育津贴能领多少钱(最新消息)厦门产假多少天2 全国婚假、产假、育儿假天数2025年新版一览表(最新) 厦门生育假多少天2025年最新标准 2025年厦门产假新规有多少 湖北产假及工资新规2025 湖北产假新规2025年最新标准?如何 江苏产假及工资新规2025最新标准 2025年江苏产假可以休多少 陕西产假新规2025年工资,最新标准 陕西产假2025年可以休多 2025年生育保险报销有时间限制吗 产假工资是生育保险支付 无锡产假多少天2025新规最新消息 2025年无锡产假98天还是15 2025年北京产假98天还是158天?北京产假新规2025年最新标准 2025黑龙江产假新规最新标准 黑龙江女性生育产假可以休多少 2025年郑州产假是几天 郑州产假多少天2025新规最新消息 北京2025年底基本完成第三代社保卡换发 安徽宣城:打造社保卡 “一卡通”应用生态圈 安徽祁门:居民“一卡通” 群众“幸福卡” 甘肃张掖:人社好声音正能量不断传递 2024厦门工伤保险缴费基数是多少?缴费比例是多少? 淮南工伤保险费率调整差额补缴是多少?2024年起工伤保险缴 茂名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怎么发放?工伤认定标准是什么? 茂名申请工伤待遇后进度如何查询?如何申请工伤认定的? 茂名职工在单位就业发生工伤后怎么办?职工发生工伤谁承担 茂名自由职业者能自己缴纳工伤保险吗?茂名工伤保险怎么缴 申请非因工伤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要注意什么?具体如何 湛江工伤保险待遇核发申办条件有哪些?具体哪些人可以报销 湛江工伤保险待遇核发申办材料要哪些? 湛江工伤保险缴费基数及比例是多少?2024-2025湛江社保工伤 肇庆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提交什么材料? 怎样能认定为工伤?肇庆工伤认定标准是什么? 江门各类工伤保险待遇申领条件一览2024 伤残待遇有个几个等 江门工伤护理、报销津贴待遇申领需要提交什么材料? 江门工伤保险待遇有哪些?2024年江门医疗待遇报销需要准备 江门工伤保险待遇怎么定?2024年江门工伤待遇分几级的?
赞助商链接
猜你喜欢

唐均:医养结合还是护养结合?
自从2015年年底国务院转发了卫计委的《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以来,“医养结合”甚至“医养融合”的话题日趋升温。在2016年两会上,这个话题也成为...[查看全文]

我国社保缴费率世界排名13 并非全球最
本报讯 近日,网络有传言称:“中国社保缴费全球最高”。据此,《人民日报》邀请其各驻外记者调查部分国家的社保支出与国民享受社保待遇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全世界173...[查看全文]
今日热点
享社保、需培训、卖初夜,各国风尘女子规
点击排行榜
- 新闻
- 观点
- 政策
- 案例
- 知识
- 办理












 2019年安康生育津贴新政策:怎么算、怎么领、
2019年安康生育津贴新政策:怎么算、怎么领、 2011学年少年儿童及大学生医疗保险申报工作的
2011学年少年儿童及大学生医疗保险申报工作的 居家养老老人如何防摔倒?委员雷杰呼吁试点住
居家养老老人如何防摔倒?委员雷杰呼吁试点住 违规行驶受伤 医保能否报销?
违规行驶受伤 医保能否报销? 2019年镇江医疗保险最新政策:缴费比例、基数
2019年镇江医疗保险最新政策:缴费比例、基数 2019年绥化失业保险金最新标准:领取条件、流
2019年绥化失业保险金最新标准:领取条件、流 2019年白山五险一金交多少钱?最低标准是多少
2019年白山五险一金交多少钱?最低标准是多少 2019咸阳养老金调整最新信息:每人每月增加48
2019咸阳养老金调整最新信息:每人每月增加48 深圳社保查询 深圳社
深圳社保查询 深圳社 济南社保查询 济南养
济南社保查询 济南养 惠州社保查询 惠州市
惠州社保查询 惠州市 汕尾社保查询 汕尾市
汕尾社保查询 汕尾市 电子社保卡升级了!最新使用教程→
电子社保卡升级了!最新使用教程→ 烟台市靠着警务室民房频被砸 疑与社保缴费纠
烟台市靠着警务室民房频被砸 疑与社保缴费纠 最牛逼的就是:将社保变成了一门生意
最牛逼的就是:将社保变成了一门生意![[安徽]新社保卡今年起全面发放 看病缴费不用跑来跑去](/uploads/allimg/130319/1_0319105I5RW.jpg) [安徽]新社保卡今年起全面发放 看病缴费不用
[安徽]新社保卡今年起全面发放 看病缴费不用 徐立凡:养老金保障不公平感从何而来?
徐立凡:养老金保障不公平感从何而来? 中国社科院郑秉文:社保制度改革 要拿出“一
中国社科院郑秉文:社保制度改革 要拿出“一 《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最新解读
《广州市职工生育保险实施办法》最新解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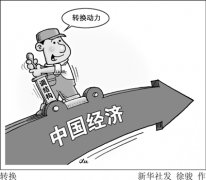 城镇职工养老金为啥有近万亿空账
城镇职工养老金为啥有近万亿空账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2015养老金双轨制废除对公务员家庭的影响
2015养老金双轨制废除对公务员家庭的影响 2019年,生育保险怎么报销?生育津贴怎么计算
2019年,生育保险怎么报销?生育津贴怎么计算 2019年绵阳市失业保险最新规定:缴费比例、基
2019年绵阳市失业保险最新规定:缴费比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