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集合主义:超越分类主义的保障政策
福利集合主义在吸收左派、右派或中间派的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在超越这些分类主义的政治思想,探讨适合自己发展的福利改革路线。福利集合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就是指国家可以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和广泛的社会政策、公共政策与经济政策一起,将福利制度与社会需求进行直接对接。福利集合主义者强调人人平等的福利社会必须通过公民权利的平等才有可能达到。他们希望以公民基本权利为基础的基础收入在将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加有效地将保守主义者强调的社会凝聚、社会自由主义者强调的自由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的再分配这三点结合起来,使社会保障能惠及更多民众。
福利集合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福利集合主义及其与社会保障政策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多种多样的意识形态中诞生了战后福利国家这样的概念。纵观整个20世纪,我们可以确认,对于一个国家中的保守主义者、社会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等持有不同理念的人来说,福利制度或者说战后福利国家这类概念的产生、发展,都对他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了这些政治理念之外,还有许多试图走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想存在。想用一个既定概念来统一称呼这些政治思想是十分困难的。虽然也有很多社会政策文献试图去统一这些概念:比如“产业主义”(Titmuss 1974)、“消极的集合主义”(George and Wilding1976)、“制度主义”(Mishra 1977)、“新重商主义的集合主义”(Pinker 1979)、“改良主义”(Taylor-Gobby and Dale 1981)和“中间路线”(George and Wilding1994)等。
“福利集合主义”这个概念,则是对过去许多社会保障学者研究见解的总称。对于社会福利制度来说,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社会基本的价值选择体系,存在着许多种类。涵盖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时代精神基础上的有区别的社会保障思想,我们用福利集合主义这样的词语来解释。
从大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将政治思想分为体制、制度思想上的对比,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选一对比。但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挫折,现在的局面又变得相当复杂。我们的目的则是将社会福利的变迁与这样的政治思想进行结合论述。社会福利的发展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存在,也就是各种政治思想中又会有怎样的福利思想?
我们试将不同学者与政治思想所对应的福利模型进行分类。美国的韦林斯基(Wilensky)最早导入了对应资本主义的“残余(residual)模型”与对应社会主义的“制度(institutional)模型”这样的概念。笛姆斯(Titmuss)进一步分为“残余福利模型”、“产业业绩福利模型”与“制度再分配模型”这三个种类。笛姆斯的模型不是简单地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分法划分,“产业业绩福利模型”对于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国家来说似乎更加合适。
马歇尔(T.H.Marshall)则将福利模型分为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主义与保守主义。平克(Pinker)与马歇尔的立场相近,但是在制度与残余两种对立的模型中间,强调第三类福利模型,即新重商主义的集合主义。集合主义(collectivism)这样的概念,英国学者用的比较多。与强调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同,它强调要建立一个能够容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向着社会主义社会方向发展的社会。
而福利集合主义的概念,也在强调可以建立一个由基础收入(Basic Income)为主的社会福利制度模型,而模型本身又兼具各种其他模型,如残余模型或者制度型模型等。很明显,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对福利集合主义这一概念施加了巨大的影响。
马歇尔在其著名的论文《公民资格与社会阶级》中,将公民资格(citizenship)分为公民权利、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三类。而只有公民同时具有三种权利时,这个国家才能够称为福利国家。
现代社会的社会福利,是伴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贫困与失业两大社会痼疾而诞生的社会对策体系。社会福利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可以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福利国家则指国家主要背负社会责任,国家是公共福利的主轴。
和贫困与失业两大社会痼疾对应,20世纪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诞生了共产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两种体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要建立福利国家,需要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消减贫困人口数量;第二步,实现福利的最大化;第三步,追求平等。换句话说,将社会保障与国家的公共补助结合在一起,建立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完全雇佣制度、包含积极方针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服务、社会收入的合理再分配以及各种财源合理分配体制的社会福利制度或者说社会福利集合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最大愿望。
当然,虽然广大社会福利学者现在赋予了这些见解或者主张以“福利集合主义”这样一个名称,但是要描绘一个政治中间派所持有的政治思想或者福利制度概念的轮廓依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将政治主张分为左派和右派,再将现在的比较社会政策分成两部分进行分析,也就是比较一下埃斯普林—安德森(Esping-Adnersen)和金斯伯格(Ginsburg)[1]的理论有何相异之处。
福利集合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要素来自不同的政治思想流派,对于这一点不同的学者进行了不同的梳理。这里,我们将费兹帕特里克(Fitzpatrick)、安德森、金斯伯格等人对福利集合主义思想来源的归纳分析作为例证在图1中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从图1中看出福利集合主义的思想要素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中所占的比重,而且可以看到,福利集合主义同时注重政治思想中激进右派与社会主义左派思想两方面。

图1福利概念的分类
当然,以上我们的讨论并不是在所有福利概念以及要素全部组合在一起时进行的,所以分类有可能并不恰当,但是并不影响我们论证的主题,即福利集合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来自于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政治思想流派。
福利集合主义的总体特征:对分类主义的超越
当我们认识到福利集合主义的思想正在进行大范围的重组再编时,针对福利集合主义的讨论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一些欧洲国家的中间左派政党,在20世纪90年代选举中所获得的优势,相比20世纪80年代来说要更加明显。由于选举的原因,这些政党在获得执政权力后,渐渐地开始弱化那些与它们处于长期对立方面的政策。因此,政治上的中间派开始逐渐产生右倾化的倾向。我们可以将这些右倾化的中间派称作“传统的福利集合主义者”,而那些希望可以将政策回归到战后福利国家这样的稍显陈旧时代的人们则被称作“市场集合主义者”。他们的政治倾向也许有一些相同,同时他们也面对着许多与以往观点截然不同的新思想不断诞生(Fitzpatrick1998b)。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对福利集合主义进行讨论的话,就必须要先将这些难以用一句话说清楚的多项复杂理论事项概括在一起。
与激进的右派不同,福利集合主义者,积极地规划着在社会公正与物质平等这一层面上的社会地位平等(Plant et al.1980)。这是因为福利集合主义者坚信,所有的大众都必须赋予满足其基本需求所必需的充足权利。[2]因为如果一个市场不受制约,则市场就必然不能向所有大众提供最低限度的尊重,也因此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地位不平等与社会分配不公平。假如资源以“依存社会全体财富量的同时,按比例分配社会全体财富”这个水准进行分配,那么在这个水准之下的人,自尊心会受到打击,也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为了保证所有的大众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社会基本财富”(自由、机会、收入、财富),为了保证所有的大众被赋予的“自然基本财富”(健康、知识、才能)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市场就必须在某种集合的统制下运营才可以(Rawls 1972)。这个时候,所谓平等的地位并不只是简简单单形式上的东西,而是指实质上的平等。所有大众都可以有获得最低保障水准物质资源以满足其基本生活所需的权利。只要社会公正的原理不受到侵犯,这样的权利就不能从社会条件中排除出去。
与激进的右派利用市场根本原理来考虑社会选择与社会需求相对,福利集合主义者则优先考虑大众的基本需要。自由市场所施行的分配制度,应当遵从于抽象的甚至非市场基准。而且,在自由市场无法充实这个非市场基准的情况下,就应该对自由市场进行规制。只有有了所有大众都可以获得基本需求这一必需条件,物质分配的平等化才可以实现。当然,这样的平等化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当基本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应该立刻停止。
这意味着,不仅仅是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等,包括福利与保障的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正当化了。[3]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福利集合主义时,必须要考虑社会阶层上的不平等。但是与左翼人士不同,大多数福利集合主义者都并不赞同,为了克服阶层上的差异就必须废除阶级,将社会生产手段改为公用制这一做法(Crosland 1956)。换句话说,即使存在社会阶级差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这样的结果,社会权利也是可以获得保障的。但是,要推进自由市场的发展,就必须要让所有人接受他们自己所必须付出的义务。因此,福利集合主义者认为,社会权利与公有制无关。社会权利是将基于个人基本必要的义务与其所得到的权利紧紧相连的一种手段、需求与选择。当所有的大众开始充实自己的基本需求,那么公众权利才有意义(Williams 1997)。
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共同体(比如政府)虽然与市场秩序连接在一起,但是两者的着眼点并不一样。政治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规制着市场经济的范围、作用与活动(Keynes1954)。福利集合主义者相信,政治共同体从属于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在支配着市场经济的运作。马歇尔这样定义福利的手段,他认为:“(没有被社会孤立的)个人被社会所接受,而他自己在接受社会这个集体所给予其福利的同时,也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Marshall 1981:91)。
换句话说,社会权利虽然是市场内部权利,但它并不是对抗市场的权利。从结果上看,福利集合主义者强调市场秩序的义务与责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对于社会福利的组织具有重要意义:
福利集合主义者主张,自由市场剥夺了那些社会贫困阶级在社会中生存时本应该获得的不可欠缺的基本需求,大多数福利集合主义者也因此批判自由市场。为了达成大众人人地位平等,市场必须以特定的形态来从属于政治共同体的运营之下。为了达成社会公正,以市场本身所可以允许的公平为标准,有必要对市场所带来的供给与负担进行再分配。社会平等,是指国家在权力范围之内,对于所有社会大众所提供均等的社会权利。而我们作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驾驭经济力量的政治共同体中的一员,社会权利是包含在市场环境当中的。也就是说,社会权利与社会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福利集合主义来看,公众权利通过对物质条件的平等化,满足大众基本生存所需。也就是说从这个观点来看,个人地位与其个人市场价值可能并不等价,而个人的社会权利与其社会义务才是对应的。那么我们必须控制市场经济内部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公这一问题,才能尽可能做到大众的社会地位尽量平等。
与过去依靠政治思想来简单划分福利国家的模型不同,福利集合主义者是在统合左派思想与右派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深化福利国家改革。如与右派学者主张根据市场经济对福利进行调节,而左派学者则主张国家统筹一切才能做到人人平等不同,福利集合主义者强调人人平等的福利社会必须通过公民权利的平等才有可能达到。但是与左派学者又不同的是,大多数福利集合主义者并不赞同,为了克服阶层上的差异就必须废除阶级,将社会生产手段改为公用制这一做法。福利集合主义者在赞同自由市场的推进可以加快大众更容易去接受公众权利与义务的同时,认为公众的社会权利来自于其必要的欲求,而自由市场的努力只是推进社会权利发展的一个助推器而已。因此,在探讨福利集合主义时往往不是探讨单纯的左派、右派或者中间派的政治思想。福利集合主义在吸收这些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在超越这些分类主义的政治思想,探讨适合自己发展的福利改革路线,这就是后文所要提到的基本收入。
福利集合主义的福利国家思想
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它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报告主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概括为“3U”思想: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即所有公民不论其职业为何,都应被覆盖以预防社会风险;统一性原则(Unity),即建立大一统的福利行政管理机构;均一性原则(Uniformity),即每一个受益人根据其需要,而不是收入状况,获得资助。
福利国家的基本定义如下:
1.以保证其公民一些基本福利为责任的国家。
2.福利国家包含一系列将货币和必需物品、服务分配给公民的制度和政策,而这个分配不建立在市场运作的基础上。
3.福利国家是那些直接运用有组织的力量(透过政治运作和行政手段)对市场力量的运作进行以下三个方向修正的国家:
(1)保证个人和家庭有一定的基本收入,而不以他们的工作和财产的市场价值为决定因素。
(2)控制“社会偶发事故”(Social Contingencies,如病、老、失业等)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不安全性的范围。
(3)保证所有公民享有能够提供的最好的社会服务,提供服务的对象和所商定的一定服务范围不以公民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归属而定。
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个福利国家所必需满足的基本需求(Basic Needs)。这里所提到的基本需求,一方面包含自然物质以及普通物质(肉体以及精神上的健康、情绪安定等),另一方面也包括社会物质。福利集合主义者认为,福利国家就是指国家可以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和广泛的社会政策、公共政策与经济政策一起,将福利制度与社会需求进行直接对接。或者说,如果国家不能满足大众的基本需求的状况一直在持续,那我们要考虑的则是,国家不是不愿意提供给大众基本需求,而是在整个社会环境和公共文化下,国家所制定的福利制度是不健全的,以至于无法满足大众。
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以上所揭示出来的这些威胁基本需求的社会问题的话,那就是“贫困”。儿乎没有福利集合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只有通过福利服务来去除贫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福利集合主义的手段来让个人或家庭直面贫困的根本原因。拒绝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保守主义者认为,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与阶级的融合,必须解决社会排斥。因此社会保守主义者拒绝自由市场经济(Macmillan 1938)。而社会自由主义者则将焦点放在个人的自由以及公共财产的分配问题上(Galbraith 1962)。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劳动者阶级的利益是根据其政治优势来确定的,这些学者强调社会正进入新资本主义时代(Crosland 1956)。当然无论理论根据是什么,福利集合主义者总是将国家福利与反贫困结合在一起。
福利集合主义与国家集合主义并不一样,福利集合主义的制度与服务是自发行为,通过商业与家庭这样的形态来进行。当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倡导福利多元主义的学者认为战后国家中心主义与中央集权化的倾向过于明显。贝弗里奇对行使过度支配权力的中央集权式行政敲响过警钟(Beveridge 1948)。
资本的私有化、国有化或者对大规模产业和自然独占的管理规制在向多元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是可以干预的。私有化对于福利来说,可以产生必要的经济成长。而国有化与管理规制则可以对于纯粹资本主义产生的市场行为进行平衡、干预与再分配。同样,为了产生“混合经济型福利”,国家需要与一些非营利组织协同配合。这里面,国家组织、公有组织、民间营利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非政府部门的相互合作,使得社会大众获得基本利益。
进一步来说,福利集合主义也同样关心个人的自我责任和努力。福利集合主义者与激进右派不同,福利集合主义者认为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构造,而需要通过集合主义的方法去解决。同时,他们对个人主义的支持也较强,这与保守主义者主张的国民这一个人主义概念,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的阶级这一个人主义概念又是不相同的。
大多数福利集合主义者认为,如果要给予一个人自立的必要机会,那么必须考虑完全雇佣政策。国家有持续提供高水平雇佣机会的义务,而个人有在四十至五十年间持续工作的责任。而新出现的市场集合主义者,则对之前的社会权利与义务进行了以下几点修正:第一,比起完全雇佣来,新出现的市场集合主义者更加强调完全雇佣的可能性(employality),为了改善劳动质量与薪酬,政府和个人必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二,个人必须适应新技术环境与新经济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始终处于劳动市场中,否则就会被淘汰。最后,传统的福利集合主义者,显然将国家义务放置在个人义务之前,但是新出现的市场集合主义者则认为个人义务必须放置在集体义务之前。
最后,福利国家在普遍主义与再分配主义之间总是左右摇摆。普遍主义强调,对于那些最需要得到保障的人们所投入的资源正在越来越少;再分配主义则强调,非贫困者被排除在分配政策之外。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普遍主义是获得大多数阶层支持的协力手段之一。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普遍主义表现了连带与社会凝聚力。
直至今日,福利国家一直在维持普遍主义与再分配主义之间的平衡,今后还将继续维持下去。那么这个存在于普遍主义与再分配主义之间的平衡是否可以更好地维系下去,福利集合主义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理论根据和论点。而社会保障系统,至少在理论上,是所有人缴纳保险金,所有人获得补助金(普遍主义);对于在理论上没有缴纳能力的最贫困者给予基本援助(再分配主义)。
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对福利国家进行如下定义:福利国家是满足社会全体人员的基本需求,与其他福利部门实行合作关系,包含普遍主义与再分配主义的多元国家。
那么这样的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系统有什么关系呢?
福利集合主义的社会保障政策
“人们并不是单纯想要获取退休金与补助金,而是认为因为支付了保险金所以应该获得退休金与补助金”(DHSS 1969:12)。
这句话看起来十分明白,但是为什么在过去与现在,依旧有那么多福利集合主义者还在研究社会保障原理呢?如果仅仅是“因为支付所以获得补助”这样的形态,那么对于社会保障来说,现金支付这样的形式就简单许多。但是“补助通过金钱支付所获取”这样的理论,对于其他大部分福利服务来说并不恰当。保障原理的潜在错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明白了,就像被指出的那样:不能支付金钱的人们将如何获得社会保障?实际上,对于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当初在构思社会保障政策之时,保障或者说保险金支付系统也不是普遍的想法。因此,福利集合主义者目前所直面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当初社会保障政策制定者的愿景中的社会保障普遍适用范围。
最初导入社会保障计划的俾斯麦的意图是怎样的呢?他为了保护那些在资本主义市场下受到侵害的男性劳动者的权利,为了不让这些人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鼓动,俾斯麦建立起来一整套社会保障制度(Rimlinger1971:112-121)。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虽然认识到了这个社会保障制度战略的本质,但是却没有办法反对。确实,最初这个战略可能带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而社会民主党采用了对于中间左派不可缺失的原理来实行社会保障。之后,英国也继承了一部分过去的社会保障制度,原因也并不全部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而是为了避免国家财政枯竭。
《贝弗里奇报告》诞生的时候,社会保障原理已经基本成型。完全雇佣成为了社会连带与经济成长的推进力。也因为政府规模缩小化,如果将补助作为一时救济来考虑也许会好些,但实际上补助却成为一个平均化的产物。如果补助是平均化的,那么根据公平原理,所缴纳的金钱也应该是一致的。并且,如果缴纳的金额是一定的话,那么为了照顾低收入者,就必须将交付金额压低在一定程度。保险金的缴纳标准调低,那么补助也就对应着被压低。结果是依赖国家补助的人增加,但是贝弗里奇并不赞同。他认为,伴随着保障系统变得更加普遍主义的同时,依赖补助的人则在减少。对于福利集合主义的问题是,如何修正贝弗里奇的缺点,如何改善社会保障制度。
根据以上来看,社会保障就是一种在市场个人主义与国家集合主义妥协下的产物(Ogus 1982)。那么问题的所在就是妥协的两种力量在社会保障中哪方更强,哪方更弱。
我们可以列举以下五点:
第一,社会保障原理可以从市场失败的危机中保护社会大众。无论市场系统如何发达,总是存在社会危机的。强制加入社会保障,也可以维持社会保障所必需的资金。
第二,社会保障是再分配的。大部分再分配是停留在一定水平之上的。从理论来说,社会保障中缴纳与补助的关系是明确的。因此,社会连带与互酬性的原理一起发展。
第三,社会保障是具有社会连带责任的。如果社会大众只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么社会保障政策就只能向不适当的方向发展。
第四,对于政府来说,增加财政收入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人们相信保险金是为了自己的福利而缴纳的,那么无论对或错,提高保险金或者增税并不一定会遭到公众反对。
最后,社会保障与市场中商业保险进行协同组合,而管理形式是单一的。
福利集合主义对基础收入的态度
什么是基础收入
基础收入(Basic Income)的基本定义是:每周乃至每月,针对所有的男性、女性、孩子,以其社会权利为基础,也就是说,无论其职业地位、工作经历、婚姻状况如何,政府都无条件地给予其补助金资助。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障改革案提案中,保障所有低收入者的基本福利似乎是共同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达成却是有一定难度的。完全的基础收入就是指无条件提供补助金资助,这就是所谓“纯粹”形态的低收入保障。部分基础收入也不需要有条件加入,但是其提供的保障金额度要小于完全基础收入,也就是说可能无法攻击被保障者的基本生活。最后一类形态是过渡基础收入,这是在向前两类基础收入发展中的过渡形态。我们可以将社会主义社会理解为向完全基础收入制度推进,社会主义与完全基础收入似乎十分相像,但是所附加的条件要严格一些。
针对基础收入的讨论
近年来,针对基础收入的讨论在社会福利相关的体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也有一部分消极的理由:21世纪,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福利制度的改革都是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福利国家改革,不是在一点两点上进行改革,而是在政策目标全体上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基础收入可能会暴露一些过去政策决定中不合理之处。当然基础收入也有积极的侧面。比如基础收入理论是最早将公众权利导入社会保障系统里的理论之一。当然,马歇尔也主张过根据公众权利来决定福利国家中大众的受补助资格。但是他的理论集中在已经就业的男性中,不包括无职者或者家庭妇女。这就属于有条件地进行补助。实际上,保障与补助的支给是根据不同的贡献与必要的原理组成的。贡献原理的问题因为有许多前提的原因,不符合一定基准的人们就被区别开来。这也就导致了大量的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
因此,如果要真正做到社会公正,则根据公众权利来确定受保障资格的基础收入原理应当可以起到不小的作用。公众权利并不是依靠其本身来证明基础收入的合理性。但是大多数对基础收入持批判态度的人都认为,无论针对公众权利进行怎样的讨论,基础收入都是不能避开的一个原则。这也是笔者强调基础收入的原因之一。
福利集合主义与基础收入
对于福利集合主义者来说,基础收入有4点好处。
第一,对于其他补助所不能触及的范围,基础收入可以达到。基础收入是无条件的补助手段,所以有着近乎100%的高补助率。也就是说基础收入确实可以提供一些社会保障所没有办法提供的补助。比如:社会保障偏重以劳动与生产活动为中心的男性中心主义,因此受到了长期批判。因为为了获得补助资格,就必须长时间进行工作,并且要向政府提供缴纳了一定数量保险金的证明。而大多数福利国家的女性长期从事家庭工作,与男性相比,她们往往无法提交这样的保险金缴纳证明。基础收入是以公民基本权利为基础的,因此基础收入承认家庭中无偿劳动的价值,也就可以将社会保障的安全网络扩展得更宽泛。换句话说,基础收入不仅仅是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同时也保障所有人的平等地位。
第二,基础收入解决了失业和贫困问题,人们因此能够更加容易地去履行他们的那些基于市场的义务。福利集合主义者通常认为这样的义务与社会权利紧紧相连(Bowen and Mayhew 1990)。因为完全雇佣经济的出现,贝弗里奇所没有看到的一些问题也就应时而生。福利集合主义者并不会像激进右派那样批判市场依赖者的缺点,他们也承认保障系统本身存在问题。基础收入最吸引福利集合主义者的是,基础收入并不会像激进右派那样去指责贫困者,而是去想办法提高工资待遇来加强劳动者的工作热情(Ashdown 1989)。也就是说,对于基础收入来说,我们可以期待基于社会公众的雇佣政策出现。
第三,基础收入将税金与补助系统合理化。比如,法定补助系统,即使财政没有陷入困难,也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纳税人与“依赖性”申请人之间产生了裂痕的同时,对于非贫困者来说也给了他们“补助”的特权。基础收入在事实上消除了纳税人与补助申请者之间的区别,也消除了财政福利与法定福利之间的区别。同时,基础收入要比保障/补助系统更加有效地将保守主义者强调的社会凝聚、社会自由主义者强调的自由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强调的再分配这三点结合起来。
最后,与第二点相似,福利集合主义者的传统后继者——市场集合主义者,比他们的先驱更加强调经济上的作用。基础收入可以缓和就业政策,降低劳动市场中的机会费用,从而向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
福利集合主义者对于基础收入的态度并不明确。基础收入在给予所有人平等地位的同时,也是一种普遍主义。但是,基础收入无视那些个人与社会全体相对的,基于大众权利与社会义务的行为。因此福利集合主义者大多不看好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实现基础收入。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福利集合主义者也不能将基础收入导入社会政策这一点完全排除在外。也有很多的福利集合主义者在修正基础收入的结论。
结论
希尔(Hill)认为“基础收入是对贝弗里奇理论最理想的发展”(Hill 1990:165)。埃克辛逊(Atksinson)则强调,一种被改良的社会保障系统,将比现存的系统有着更强的社会包容力。换句话说,将更多的低收入者加入到社会保障适用范围内,将更多过去一度被排除在保障适用范围之外的人重新纳入保障范围内,对新的社会保障系统来说是必须也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社会保障原理放置在图2的两极中间的话,那么社会保障应当会向支付保险金这一极显著倾斜。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这一情况。在福利集合主义者之间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社会保障必须向大众权利这一极有更多倾斜。这也是新贝弗里奇学派的理论目的之一。

图2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么发展成完全的基础收入也不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对于这一点,福利集合主义者也在考虑将来有一天基础收入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注释:
[1]金斯伯格将福利概念分为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市场两种模式。而安德森则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集团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三类福利国家概念模型。
[2]米勒(Miller)和高夫(Gough)曾经论述过社会的公正与基本需求这一问题。
[3]这是对福利的平等权利:平等权利并不是无视高物价的东西(Dworkin 1981;Arneson 1989),而是最大限度地保持全体公民在一定水准下的福利权利。
参考文献:
[1]Atkinson, A., (1993), “Participation Income,” Citizens Income Bulletin, No. 16, pp.7-11.
[2]Atkinson, A., (1995), Incomes and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Atkinson, A., (1996), “The Case for a Participation Incom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67, No. 1, pp. 67-70.
[4]Beveridge, W., (1942),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London:HMSO.
[5]Beveridge, W., (1944),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Geroge Allen & Unwin.
[6]Crosland, A., (1956),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7]Fitzpatrick, T., (1998), “New Welfare Associations:An Alternative Model of Well-Being,” Storming the Millennium:A New Polities of Chang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8]Fitzpatrick, T., (1998),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in Lent, A., ed., New Political Thought:An introduction,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9]広井良典、駒村康平編:(2003),《アジアの社会保障》,東京大学出版会。
[10]広井良典:(2006),《持続可能な福祉社会》,ちくま新書。
[11]新川敏光、G.ボノ一リ:(2004),《年金改革の比較政治学》,ミネルヴァ書房。
[12]G.ェスピン一アンデルセン編:(2003),《転換期の福祉国家》,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13]武川正吾:(2007),《連带と承認》,東京大学出版会。
[14]武川正吾:(2006),《福祉社会の価值意識》,東京大学出版会。
[15]橘木俊詔編:(2007),《政府の大きさと社会保障制度》,東京大学出版会。
[16]宮本太郎編:(2006),《比較福祉政治》,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17]齊藤純一:(2004),《福祉国家/社会的連带の理由》,ミネルヴァ書房。
[18]桂木隆夫:(2005),《公共哲学とはなんだろぅ—民主主羲と市埸の新しい見方》,勁草書房。
“福利集合主义:超越分类主义的保障政策”由中国社保网收集整理编辑。
本文地址:http://www.shebaodata.com/guandian/8519.html
为了社保知识的普及、信息的传播,中国社保网欢迎您转载分享。但请注明文章出处并保留完整链接。否则我们将保留追究其版权责任的权利!
社保常见问题答疑
最新刊登
- 苏州单位社保缴纳个人一年4314元,缴纳23年退休工资一个月 2025社保退休工资计算公式 四川眉山养老金计算公式2025计算 社保交33年退休金今年有多少?(2月5日) 2025年,养老金即将上涨,工龄27年、32年、37年,领的钱差 湖南益阳退休人员2024年养老金计发基数出炉 养老金重算补发 广东佛山交16年养老保险每个月能领多少? 申领失业保险金需提供的材料?大理的申请失业金材料要求一 2025阿勒泰退休工资计算公式,27年退休金多少钱? 社保缴费24、29、32年区别有多大,谁领的养老金多? 喀什退休金计算公式2025,16年能享受到多少养老金呢? 25年工龄退休工资是多少?(2月5日) 退休金和养老金有区别吗?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金多少钱一个月 社保缴纳年限有何要求?福鼎社保多少钱一个月2025年? 2025年,养老金即将上涨,工龄28年、31年、32年,领的钱差 公积金房贷利率会自动调整吗?静安调整时间是什么时候? 2023-2025年湖北咸宁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湖北咸宁社保需要缴 2025南京退休养老金账户金额怎么计算的?个人账户养老金计 东方社保交28年可以领多少退休工资? 青海西宁退休金计算方法,缴纳攻略如何交更划算你知道吗? 昌都住房公积金单位和个人缴纳比例是多少?有封顶吗?最高 线下办理失业金领取需要本人吗?伊犁的失业金领取要求? 社保缴纳20年,能有多少退休金?(02/05) 北京养老金重算补发,哪些人能领取?北京养老金计算公式是 社保交满15年每月领多少钱?19年、24年和29年工龄退休分别 2024~2025年陕西榆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最新标准(申请条件+ 运城缴纳200%档26年社保,领多少养老金?(25年2月5日) 2024-2025年新乡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价格表 新乡灵活就业 社保交满37年、40年和42年退休,哪个退休金高?举例说明 浙江衢州养老金计算公式2025年计算举例 2025年浙江衢州退休 解密2023年甘肃金昌养老金计发基数之谜,养老金迎来重算补 社保断交后可以补交吗?(02/05/25) 灵活就业自己交社保一个月要交多少钱?02/05/25 鹤岗交多少个月失业保险可以领失业金? 2025年鹤岗失业金领 2025年汕头五险一金的缴费基数是多少(缴费基数+缴费比例) 换工作期间社保断交一个月怎么办?(2月5日) 公积金利率下调2024,山西晋城2024年贷款利率,房贷100万利 住房公积金个人缴费上限是多少?广东韶关公积金2024年缴费 陕西延安社保待遇认证怎么在手机上完成?最新教程来了(怎 汕尾4050社保补贴标准最新消息 2025年汕尾灵活就业4050补贴 2025安康社保缴费标准一览表(2025-02-05) 失业金停止领取的条件是什么?2024年景德镇的失业金申领条 天津交灵活就业社保与职工社保有什么不一样?天津灵活就业 永州社保缴纳到退休能领到多少钱?2024-2025年永州社保缴费 贵港失业保险金怎么申领?来看→ 公积金贷款利率2024最新消息 克州首套房五年以上公积金贷款 武威公积金缴纳比例基数是多少?最新住房公积金基数何时调 防城港4050社保补贴多少钱一个月,2024-2025年4050社保补贴 南充公司社保可以不交吗? 社保中断了几年还能续交吗?(2月5日) 谁能领失业保险金?海拉尔失业金领取要求标准 社保断了七八年能续交吗?(25年2月5日) 社保缴纳基数是按照实发工资还是应发工资缴纳?个人需要交 广东河源社保缴费比例是怎样的?广东河源社保计算公式一览 2025新农合怎么报销?2025年新农合的报销流程和标准是多少 最新保亭公积金缴纳标准一览表,2024-2025年公积金缴纳基数 离职失业金怎么领取?承德的失业保险金申请要求 内蒙古乌兰察布房贷利率调整新消息 现在 内蒙古乌兰察布存 2024-2025年东城灵活就业社保每月需要多少钱?自费灵活就业 2024~2025年张家口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最新标准(申请条件+申 2025社保个人缴费标准多少钱,社保个人缴纳多少钱一个月? 社保断交就作废了吗?2025年南充社保多少钱一个月? 文山市失业金怎么领取需要什么条件和手续?这里整理收好了 2025昌都社保缴纳比例是怎样的?(2025年2月5日) 2025年商洛公积金个人公积金缴存多少?商洛公积金缴存基数 2024~2025年烟台灵活就业4050补贴最新标准 烟台灵活就业社 2024-2025年阿拉尔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标准:自费社保需要 张家口失业金领取条件及标准 最新张家口失业保险金在哪里可 曲靖申领失业保险金需提供的材料哪些? 2025年柳州社保缴纳比例,2025年柳州社保缴费多少钱?2025 公积金利率下调2024,安徽阜阳2024年贷款利率,房贷100万利 2024公积金缴费基数是多少 襄阳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 2024~2025年辽源4050社保补贴标准是多少钱一个月(失业金和 2025社保缴纳比例是怎样的?(2025年2月5日) 河北衡水失业金申请方式有几种? 社保缴纳多少年可以领养老金?(2月5日) 养老保险断交了3年怎么办?社保断交有什么影响?(2025年2 打工人缴纳社保缴费多少钱?2025年2月5日 2025铜仁社保缴费基数和比例是多少呢?(02/05) 西宁个人社保一个月多少钱?(2025/02/05) 社保一个月交多少钱,在职人员缴纳多少钱一个月?(02/05) 养老金什么时候发,有统一时间吗?02/05 安阳社保多少钱一个月?(02/05) 社保和农保都交了怎么办?(25年2月5日) 怎么算每个月五险一金扣了多少?(02/05) 2025北京社保缴费标准及比例是多少?(25年2月5日) 社保断交有什么影响个人可以补吗?(2025年2月5日) 社保停了几年怎么续交(02/05/25) 铁门关灵活就业人员社保一个月交多少钱?2025年2月5日 五险一金扣多少钱一个月 五险一金每月缴费怎么算?(02/05 退休养老金计算公式是怎样的?02/05/25 社保断交多久就作废了?(02/05) 浙江社保多少钱一个月?(2025-02-05) 换工作中间断了一个月社保怎么办?社保缴纳多少年可以领取 社保卡过期了?教你如何轻松换卡?(2025年2月5日) 2022银行购房贷款利率调整时间 西双版纳新商贷利率定价机制 申领失业保险金需提供的材料?娄底的申请失业金材料要求一 失业金在哪里怎么申请领取?最新吉林松原的失业金领取条件 上调吗?陵水公积金年度调整开始!有何变化? 上海失业金支付宝怎么申请领取流程?附失业保险金办理操作 云南大理2024年买房贷款利率怎么计算?房贷90万分30年本息 失业咋办?失业保险谁能领?长兴失业金领取标准 丰都公积金缴存基数怎么计算的?2024住房公积金基数工资标 张家口的失业保险金怎么申请?附失业金微信申请流程图 广东梅州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怎么查?2024首套、二套房公积 领失业金需要带什么材料?看看武威失业保险金办理材料一览 汕头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最新),2024-2025年汕头公积金个 内蒙古呼伦贝尔怎样在手机上申领失业保险金?支付宝领取失 公积金利率下调2024,河南洛阳2024年贷款利率,房贷100万利 抚顺公积金缴纳比例基数表 2024个人缴存一个月多少钱? 贵州遵义失业金发放标准提高?查询一下 贵州遵义失业金领取 贵港失业金领取标准2024年 贵港失业金领取金额怎么算? 青海海东房贷利率调整新消息2024 青海海东公积金商业贷款利 2025年丰县失业保险金线下可以办理吗?具体怎么操作? 2024-2025年银川职工住房公积金要交多少(缴费比例+缴费基 失业金怎么申请领取?掌握一下领取聊城的失业保险金要求? 2025年石嘴山失业保险金能线上申领吗?办理入口都有哪些? 更灵活!个人房贷利率重新定价了!广东茂名存量房贷利率调 静海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定了么?2025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 2025年乌兰察布申领失业保险待遇,需提交哪些材料? 公积金利率下调2024,山东济南2024年贷款利率,房贷100万利 甘肃张掖:甘州区人社局为群众奉上人社“自助餐” 2025年新农合报销比例最新标准是多少 新农合门诊报销和住院 65岁老人住院报销比例是多少 新农合65岁以上的老人住院报销 新农合医保报销比例2025最新标准,最新消息 2025农村医疗保 深圳退休医保按月或一次性补缴要缴多少?哪种方式更好? 退休人员医保将有变化!2025年起医保划转金额提高能有多少 2025年起,退休人员医保划转金额有提高,能涨多少?提前了 2025年医保返款标准调整,退休人员年满70岁,返款金额能有3 2024年退休人员,医保个人账户返款标准有多少?会有所增加 2025年退休后医保卡每月打多少钱 2025年起医保划转金额新变 山西晋城:让就业社保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新农合(医疗保险)报销比例2025年最新标准,最新消息 新农合异地就医可以报销吗?2025年新农合异地就医报销流程 新农合异地就医报销流程2025最新消息 新农合异地就医可以报 新农合异地就医报销流程2025年最新是什么 新农合异地就医可 2025年新农合报销标准及范围是多少 最新标准 新农合医保报销比例2025最新标准是多少 2025农村医疗保险如 新农合门诊报销和住院报销标准多少?2025年新农合报销比例 2025年新农合生孩子可以报销多少?2025年新农合生孩子报销 新农合报销比例最新标准多少?2025年新农合门诊报销和住院 新农合报销标准及比例2025最新消息,最新标准 2025年新农合缴费价格是多少钱?新农合报销比例2025年最新 新农合二次报销标准及比例是怎么算的 2025年哪些情况不能报 生孩子新农合报销范围及标准最新消息 2025生孩子新农合可以 甘肃张掖:甘州区失业保险强服务 助企纾困促发展 2025年全国产假新规有多少天 2025年职工最长休假达1年(最 2025年厦门生育津贴能领多少钱 厦门产假多少天2025年新规( 重庆生育津贴领取条件及标准2025最新 重庆生育津贴128天还 2025生育津贴领取条件及标准 生育津贴2025年新规最新消息 2025年最新生育津贴领取条件及标准是什么 2025年生育保险报销最新标准 生育保险报销条件是什么 杭州生育津贴领取条件及标准2025年最新(领取条件+领取标准 2025生育保险领取要满足哪些条件?不生孩子生育保险就白交 广东产假法规2025年最新标准 广东省产假2025年能休多少天 浙江生育假多少天2025年新规最新消息 浙江产假2025年有多少 产假及工资新规2025 产假多少天2025年新规(最新标准) 全国产假新规2025年有多少天 2025年职工产假最长休假达1年 2025年厦门生育津贴能领多少钱(最新消息)厦门产假多少天2 全国婚假、产假、育儿假天数2025年新版一览表(最新) 厦门生育假多少天2025年最新标准 2025年厦门产假新规有多少 湖北产假及工资新规2025 湖北产假新规2025年最新标准?如何 江苏产假及工资新规2025最新标准 2025年江苏产假可以休多少 陕西产假新规2025年工资,最新标准 陕西产假2025年可以休多 2025年生育保险报销有时间限制吗 产假工资是生育保险支付 无锡产假多少天2025新规最新消息 2025年无锡产假98天还是15 2025年北京产假98天还是158天?北京产假新规2025年最新标准 2025黑龙江产假新规最新标准 黑龙江女性生育产假可以休多少 2025年郑州产假是几天 郑州产假多少天2025新规最新消息 北京2025年底基本完成第三代社保卡换发 安徽宣城:打造社保卡 “一卡通”应用生态圈 安徽祁门:居民“一卡通” 群众“幸福卡” 甘肃张掖:人社好声音正能量不断传递 2024厦门工伤保险缴费基数是多少?缴费比例是多少? 淮南工伤保险费率调整差额补缴是多少?2024年起工伤保险缴 茂名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怎么发放?工伤认定标准是什么? 茂名申请工伤待遇后进度如何查询?如何申请工伤认定的? 茂名职工在单位就业发生工伤后怎么办?职工发生工伤谁承担 茂名自由职业者能自己缴纳工伤保险吗?茂名工伤保险怎么缴 申请非因工伤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要注意什么?具体如何 湛江工伤保险待遇核发申办条件有哪些?具体哪些人可以报销 湛江工伤保险待遇核发申办材料要哪些? 湛江工伤保险缴费基数及比例是多少?2024-2025湛江社保工伤 肇庆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时应当提交什么材料? 怎样能认定为工伤?肇庆工伤认定标准是什么? 江门各类工伤保险待遇申领条件一览2024 伤残待遇有个几个等 江门工伤护理、报销津贴待遇申领需要提交什么材料? 江门工伤保险待遇有哪些?2024年江门医疗待遇报销需要准备 江门工伤保险待遇怎么定?2024年江门工伤待遇分几级的?
赞助商链接
猜你喜欢

社保费用统一由税务部门征收,目的很明
今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明确从2019年1月1日起,将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各项社会保险费交...[查看全文]

社保距离“全国漫游”还有多远(图)
那么,下一步,作为拥有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网的中国,如何让社保基金运行得更规范、社保何时能进入“全国漫游”时间、养老金“双轨制”如何并轨?代表委员对此发表了看法。...[查看全文]
今日热点
享社保、需培训、卖初夜,各国风尘女子规
点击排行榜
- 新闻
- 观点
- 政策
- 案例
- 知识
- 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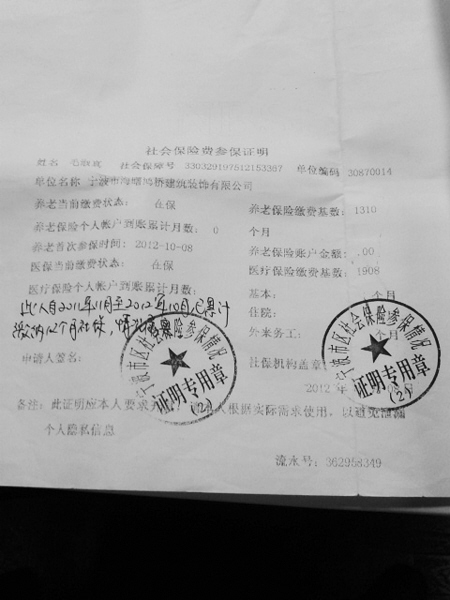





 江西生育服务系统
江西生育服务系统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解读 下个
《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解读 下个 社保基金谋扩容 部分国有产权有望“入列”
社保基金谋扩容 部分国有产权有望“入列” 浙江农信社社保卡如何贷款?浙江农信社社保卡
浙江农信社社保卡如何贷款?浙江农信社社保卡 2024年度阳江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生育保险缴
2024年度阳江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生育保险缴 发改委学者建议今年开始延迟退休:每年增加1
发改委学者建议今年开始延迟退休:每年增加1 2019年辽阳失业保险最新规定:缴费比例、基数
2019年辽阳失业保险最新规定:缴费比例、基数 2019年张家口工伤保险最新规定:赔偿标准、范
2019年张家口工伤保险最新规定:赔偿标准、范 深圳社保查询 深圳社
深圳社保查询 深圳社 济南社保查询 济南养
济南社保查询 济南养 惠州社保查询 惠州市
惠州社保查询 惠州市 汕尾社保查询 汕尾市
汕尾社保查询 汕尾市 调查显示:大多数网民赞成废除养老双轨制
调查显示:大多数网民赞成废除养老双轨制 细数美国养老金八大特色
细数美国养老金八大特色 延迟退休一年养老金增40亿 被批是杀鸡取卵策
延迟退休一年养老金增40亿 被批是杀鸡取卵策 英媒:不灵活和不公平的中国社保体制
英媒:不灵活和不公平的中国社保体制 记者逼问中国进攻钓鱼岛怎么办 奥巴马苦笑
记者逼问中国进攻钓鱼岛怎么办 奥巴马苦笑 医保参保人可以在医保定点药店刷卡买药吗?可
医保参保人可以在医保定点药店刷卡买药吗?可 运城医疗保险查询
运城医疗保险查询 2016年上海产假最新规定:正常产假98天
2016年上海产假最新规定:正常产假98天 一图看懂《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一图看懂《城企联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江苏省关于2018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江苏省关于2018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事业单位人员将统一交社保
事业单位人员将统一交社保 抚州社保查询 抚州养老金查询 抚州社保网 抚
抚州社保查询 抚州养老金查询 抚州社保网 抚